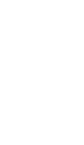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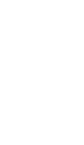
六十八岁这年,我以为日子就像院里那棵老核桃树,再结不出什么新果子,只剩下安安稳稳地落叶归根。
我叫陈建军,一个在山脚下跟木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木匠。
腿脚还算利索,每周上山采点草药,是我雷打不动的习惯。
给我那口子,还有城里的儿子陈辉寄过去。
这天雾大,山里湿漉漉的,像刚哭过一场。
我背着竹篓,在半山腰一块青石板上歇脚。
山风穿过松林,带着哨音,吹得人骨头缝里都凉。
就在我拧开水壶,准备喝口热茶的时候,石头另一侧,飘来了两个女人的说话声。
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,起初我没在意。
“……烦死了,每周末都得回来演戏,那老房子一股霉味。”
这个声音年轻,带着点不耐烦的娇嗔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另一个声音略显成熟,劝慰道:“再忍忍,小林,等房本名字一改,钱一到手,你还管他们老的死活?”
小林。
我的儿媳妇,就叫林雪。
我浑身的血,像是瞬间被抽干了,又猛地冲回头顶。
耳朵里嗡嗡作响。
我屏住呼吸,像一块石头,一动不动地贴在石板后面。
“可陈辉那人死心眼,非说要等他妈身体好利索了再说。我看他就是拖着,不想把那套老房子卖了。”
林雪的声音。
我不会听错。
那个成熟的声音笑了声:“男人嘛,都恋家。你得有耐心,温柔刀,慢慢磨。你不是说,他最听你的话了吗?”
“听话是听话,可一提到他爸妈,就跟上了锁似的。上次我提了一句,想把他们接到城里那个小次卧,他脸拉得跟驴一样长。说他爸离不开那堆破木头,他妈住不惯楼房。”
“傻姑娘,谁让你真接了?姿态要做足。你得让他觉得,你心里是有他父母的。至于那套老房子,地段那么好,又是学区,卖了少说能换二百万。你目前住的那套,贷款不就全清了?剩下的钱,你开个小工作室,不比看人脸色强?”
我的手,死死攥着水壶,壶身滚烫,我却感觉不到。
二百万。
那是我们老两口住了四十年的根。
“芳姐,还是你懂。我就是觉得憋屈,凭什么啊?我嫁给他,图什么?不就图个安稳。目前倒好,我还得伺候他那一大家子。他爸那个倔脾气,我多说一句话都嫌我吵。”
“所以啊,钱拿到手最实在。你记住,眼泪是女人的武器。回去多跟他吹吹风,说你同事谁谁谁,老公给换了新车;谁谁谁,又出国旅游了。男人要面子,经不住这个。”
“嗯,我知道了。等下山我还得去买他妈爱吃的那个牌子的点心,想想就烦。”
“演戏嘛,就要演全套。”
脚步声渐渐远了。
我靠在冰冷的石板上,山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脸。
竹篓里的草药,散发着清苦的味道。
我采了半天的“伸筋草”,希望能让我老婆子的腿脚好受点。
可目前,我只觉得,这世上最难治的,是人心里的病。
我猛地站起来,头一阵发晕。
也顾不上收拾东西,背起竹篓,几乎是踉跄着,朝山下冲去。
我得回去。
我得亲眼看看,我那个被夸“懂事孝顺”的儿媳妇,到底长了一副什么样的心肠。
两天前。
那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周五晚上。
陈辉带着林雪,像往常一样,从市里开车回来。
我老婆子张罗了一大桌子菜,炖了儿子最爱喝的排骨汤。
饭桌上,林雪的话不多,总是带着浅浅的D笑。
她会给我老婆子夹菜,轻声细语地说:“妈,您多吃点这个,补钙。”
也会笑着看我,说:“爸,您这手艺,比外面五星级酒店的大厨都强。”
那时候,我看着她清秀的脸,心里是熨帖的。
觉得儿子有福气,娶了个知书达理的好媳'fu。
陈辉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技术主管,忙得脚不沾地。
林雪在一家外企做会计,工作体面,人也美丽。
他们结婚五年,还没孩子。
林雪说,想等事业再稳定一点。
我和老婆子虽然着急抱孙子,但也不好催得太紧,总觉得年轻人的事,由他们自己做主。
为了他们结婚,我们把城里单位分的旧房子卖了,凑了八十万,给他们付了新房的首付。
当时,陈辉要把我们的名字也加到房本上。
林-雪笑着说:“爸,妈,不用了。你们的钱,就是我们的钱。写谁的名字都一样,都是一家人。”
她话说得美丽,我和老婆子心里感动,便也没再坚持。
目前想来,那句“写谁的名字都一样”,真是充满了讽刺。
吃完饭,陈辉被公司一个电话叫去书房处理工作。
林雪陪着我老婆子在客厅看电视,一边看,一边漫不经心地削着一个苹果。
“妈,您这腿,最近好点没?我给您在网上买了个按摩仪,明天就寄到了。”
我老婆子笑得合不拢嘴:“好,好,还是小雪贴心。”
我坐在一旁的老藤椅上,默默地抽着烟。
看着眼前这幅“婆慈媳孝”的画面,心里却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,扯得生疼。
那些在山上听到的话,像电影画面一样,一帧一帧地在我脑子里回放。
“演戏嘛,就要演全套。”
我看着林雪递给我老婆子的那块苹果,果肉晶莹,削得干干净净。
可我只觉得,那上面沾满了看不见的毒。
我把烟掐了,站起身。
“我出去走走。”
老婆子问:“这么晚了,去哪啊?”
“院子里透透气。”
我走到院子里,晚风清凉。
那棵老核桃树的叶子,在月光下泛着银光。
这院子,这房子,是我亲手一砖一瓦盖起来的。
每一根梁,每一扇窗,都刻着时间的痕迹。
这里,是我的根,是我和我老婆子老了之后的念想。
可目前,它在别人的算计里,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变现的数字。
二百万。
我靠在冰冷的墙上,第一次感觉到了,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。
这种无力,比年轻时扛几百斤的木料还要沉重。
我不是没见过人心的复杂。
做了一辈子木匠,什么样的木头没见过?
有的木头,看着光鲜亮丽,内里却早就被虫蛀空了。
有的人,是不是也一样?
我深吸一口气,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我不能慌。
慌,就乱了阵脚。
这件事,我不能直接告知我老婆子,她心脏不好,受不住这个刺激。
我也不能直接去质问陈辉,他性子急,一冲动,这个家可能就散了。
我得找到一个办法。
一个能保住这个家,也能让我儿子看清楚他身边的人,到底是什么样的办法。
我需要证据。
虽然我亲耳听见了,但在他们面前,这只是我的一面之词。
林雪那样的人,巧舌如簧,没有铁证,她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
我回到屋里,他们已经各自回房休憩了。
客厅的灯关了,只有电视机还亮着,屏幕上闪烁着无声的广告。
我走过去,关掉电视。
黑暗中,我仿佛看到一张巨大的网,正悄无声息地笼罩着我们这个家。
而我,必须要做那个,戳破这张网的人。
第二天是周六。
我起得很早,像往常一样,在院子里打了一套太极。
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在地上,斑斑驳驳。
一切看起来,都和昨天没什么不同。
但我知道,有什么东西,已经彻底碎了。
吃早饭的时候,林雪果然提起了按摩仪的事。
“爸,妈,我给你们买的按摩仪,今天应该能到。到时候你们试试,对关节好。”
她笑得一脸真诚。
我老婆子连连说好。
我只是“嗯”了一声,低头喝着粥。
我看到陈辉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。
他大致又为了工作,熬了半宿。
我心里叹了口气。
我这个儿子,什么都好,就是太实诚,太信任人了。
他以为他娶的是爱情,却不知道,对方可能只是把他当成了一块跳板。
早饭后,陈辉要去镇上见个老同学。
林雪说她头有点疼,想在家休憩。
机会来了。
我看着陈辉的车开出院子,然后转身回了屋。
林雪正躺在沙发上,盖着毯子,刷着手机。
我走过去,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
她抬头看了我一眼,笑了笑:“爸,您有事?”
“小雪啊。”我开口,声音尽量放得平缓,“你和陈辉结婚,也有五年了吧?”
她愣了一下,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。
“是啊,爸,五年了,时间过得真快。”
“五年了,不短了。”我看着她的眼睛,“当初你们买房,我们老两口把积蓄都拿出来了。我们不图你们什么,就图你们能过得好,能安安稳稳的。”
林雪的脸色微微变了变,但还是维持着笑容。
“爸,您说这个干什么。您和妈对我们的好,我们都记在心里呢。”
“记在心里?”我笑了笑,那笑容里,肯定带着几分苦涩,“我怎么觉得,你记在心里的,是这套老房子能卖多少钱呢?”
空气,瞬间凝固了。
林雪脸上的笑容,像石膏一样,僵住了。
她的眼睛里,闪过一丝慌乱,但很快就被掩饰过去。
“爸,您……您这是什么意思?我听不懂。”
“听不懂?”我从口袋里,摸出我的那部老年机。
我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,但我让邻居家的孙子,教我怎么用录音。
我按下了播放键。
“……烦死了,每周末都得回来演戏,那老房子一股霉味。”
林雪的声音,清晰地从手机里传了出来。
她的脸,在一瞬间,变得惨白,毫无血色。
她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,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手机,像是要把它看穿一样。
录音还在继续。
“……再忍忍,小林,等房本名字一改,钱一到手,你还管他们老的死活?”
“……那套老房子,地段那么好,又是学区,卖了少说能换二百万。”
每一句话,都像一把锤子,狠狠地砸在林雪的脸上。
她的身体开始微微发抖,嘴唇哆嗦着,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我关掉了录音。
客厅里,静得可怕。
只听得见墙上老挂钟,滴答,滴答,走动的声音。
像是在为我们这段破碎的亲情,倒计时。
“目前,听懂了吗?”我问她,声音不大,但每一个字,都像钉子一样,钉进她的心里。
林雪的眼睛里,终于涌上了泪水。
但那不是悔恨的泪,而是恐惧和羞愤。
“你……你跟踪我?你偷听我说话?”她声音尖利,带着质问。
“我还不至于那么下作。”我看着她,眼神冰冷,“我只是碰巧,在山上,听到了不该听的话。”
“我……”她张了张嘴,想辩解,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。
录音,是铁证。
“我没有,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她开始语无伦次,“我就是……就是跟同事抱怨几句,你知道的,工作压力大……”
“抱怨?”我打断她,“抱怨要把我们的房子卖了?抱怨演戏给你演烦了?抱怨我们老两口是你的累赘?”
我的声音,不由自主地提高了。
胸口那股压抑了两天的火,终于烧了起来。
“林雪,我们老陈家,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,但也是清清白白的。我们拿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疼,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?”
“我……”她被我问得哑口无言,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
“你别哭。”我冷冷地说,“你的眼泪,在我这里,一文不值。我今天跟你说这些,不是为了听你道歉,也不是为了看你哭。”
我站起身,走到她面前。
“我只问你一件事。”
我盯着她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问:“你对陈辉,还有没有一点真心?”
她抬起头,泪眼婆娑地看着我,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
有惊恐,有乞求,也有一丝,被我看穿的狼狈。
“我……我爱他。”她哽咽着说。
“爱他?”我冷笑一声,“爱他,就是算计他的家产?爱他,就是把他父母当成你奔向‘好日子’的垫脚石?”
“我不是!”她激动地反驳,“我是为我们好!目前生活压力多大,你知不知道?陈辉每天加班到半夜,他那么辛苦,我想为他分担一点,这有错吗?”
“分担?”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,“你的分担,就是把他家掏空,然后一脚把他踹开?”
“我没有想过要踹开他!”
“那你跟你的芳姐说,‘钱一到手,还管他们老的死活’,是什么意思?”我步步紧逼。
林雪的脸,又白了一分。
她大致没想到,我连那个人的名字都知道。
她彻底说不出话了,只是坐在那里,无声地流泪。
我看着她,心里没有一丝怜悯。
哀莫大于心死。
我对这个儿媳妇,最后一点情分,也在这场对峙中,消磨殆尽了。
“行了。”我摆了摆手,重新坐回椅子上,“目前,我们来谈谈,这件事,怎么解决。”
我的冷静,似乎让她更加害怕。
她抬起头,用一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着我。
或许在她眼里,我一直是个沉默寡言,没什么主见的老头子。
她从没想过,我会如此强硬,如此……不留情面。
“你想怎么样?”她声音发颤。
“我不想怎么样。”我说,“我只想保住我儿子的家,保住我们老两口的根。”
我顿了顿,看着她的眼睛,说出了我的条件。
“第一,城里那套房子,必须加上陈辉的名字。而且,要去公证处做一份协议,写明购房款里,有我们老两口出的八十万。如果你们将来……分开了,这笔钱,要原封不动地还给我们。”
林雪的瞳孔,猛地收缩了一下。
这是打在了她的七寸上。
“第二,这套老房子,你后来,一个字都不许再提。这是我们的,跟你们没关系。我们就是死了,也是留给陈辉的,跟你,没关系。”
“第三……”我看着她,缓缓地说,“你要真心实意地,跟陈辉过日子。如果你做不到,或者让我再发现你有什么别的心思……”
我没有说下去。
但我的眼神,已经告知了她后果。
林雪的脸色,变了又变。
从惨白,到涨红,再到死灰。
她知道,我这不是在跟她商量。
这是通牒。
“如果……如果我不同意呢?”她挣扎着,问出了最后一句话。
“你不同意?”我看着她,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,“那我就把这段录音,放给陈辉听。你觉得,以他的脾气,他会怎么做?”
“你觉得,你们这个婚,还离得成吗?你还能分到一分钱的财产吗?”
“你别忘了,婚内欺骗,转移财产,在法律上,是什么后果。”
这些话,不是我懂的。
是前天晚上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给我那个当律师的远房侄子打电话,一个字一个字问来的。
我活了快七十年,从没想过,有一天,要用这些冰冷的条条框框,来对付自己的家人。
真是莫大的悲哀。
林雪彻底崩溃了。
她瘫在沙发上,放声大哭。
哭声里,有绝望,有不甘,但更多的,是计划败露后的恐惧。
我没有安慰她。
我只是静静地坐着,抽着烟,等她哭完。
我知道,从今天起,我们这个家,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
就算表面上还能维持和平,但那道裂痕,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每个人的心里。
永远,也无法弥补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林雪的哭声渐渐小了。
她抬起红肿的眼睛,看着我,声音沙哑。
“我……我答应你。”
我点了点头,掐灭了烟。
“好。”
就在这时,院门外,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。
是陈辉回来了。
林雪的身体,猛地一僵。
她慌乱地擦着眼泪,整理着自己的头发和衣服。
“爸,求求你,别告知陈辉,行吗?”她哀求地看着我,“我保证,我后来再也不会了。你告知他,我们……我们就完了。”
我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,心里没有半分动容。
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。
但我还是点了点头。
“我暂时,不会告知他。”
我说的是“暂时”。
主动权,目前在我手里。
“你最好,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”
我站起身,朝门口走去。
陈辉推门进来,看到客厅里的气氛,愣了一下。
“爸,小雪,你们这是怎么了?”他看到林雪红肿的眼睛,立刻紧张起来,“小雪,你哭过了?是不是哪里不舒服?”
他快步走到林雪身边,关切地问。
林雪低下头,摇了摇头,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
“没事,就是……就是想家了。”
一个多么拙劣的借口。
但陈辉信了。
他心疼地搂住林雪的肩膀,柔声安慰她。
“傻瓜,想家了就回去看看。下周我陪你回去。”
我看着眼前这一幕,只觉得无比刺眼。
我的儿子,像个傻子一样,心疼着一个处心积虑算计他的女人。
而我,这个知道真相的人,却只能像个哑巴一样,站在一旁,看着他们演戏。
我转身,走进了我的木工房。
关上门,隔绝了客厅里的一切。
木工房里,充满了木屑和桐油的味道。
这是我最熟悉,也最安心的味道。
我拿起一块还没雕刻完的樟木,拿起刻刀。
但我的手,却抖得厉害。
一刀下去,划偏了。
木头上,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。
就像我的心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,气氛很诡异。
我老婆子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,但她没多问,只是一个劲地给陈辉和林雪夹菜。
林雪低着头,默默地扒着碗里的饭,一句话也不说。
陈辉几次想开口缓和气氛,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只有我,像个没事人一样,该吃吃,该喝喝。
但我知道,桌子底下的那片暗流,有多么汹涌。
吃完饭,陈辉和林雪没有多待,就开车回城里了。
临走前,林雪看了我一眼。
那眼神里,有恐惧,有怨恨,还有一丝……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的车,消失在村口的小路上。
老婆子走到我身边,叹了口气。
“老头子,你是不是跟小雪说什么了?我看那孩子,魂不守舍的。”
我转过身,看着她花白的头发,和满是皱纹的脸。
我不能让她知道。
至少目前不能。
“没什么。”我拍了拍她的手,“就是跟她说了几句,让她跟陈辉好好过日子,别老想着工作,该要个孩子了。”
老婆子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,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
“是该要个孩子了。有了孩子,家才算完整。”
我望着远处的天空,心里一片茫然。
家?
我们这个家,还完整吗?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过得异常平静。
平静得,让人心慌。
周一,我给那个律师侄子打了电话,把我的要求跟他说了。
他很快就草拟了一份协议,通过微信发给了我。
我让邻居家的孙子,帮我打印了出来。
我看着那份白纸黑字的协议,上面充斥着“甲方”、“乙方”、“财产分割”、“违约责任”这些冰冷的词语。
心里说不出的不舒服。
我一个老木匠,一辈子跟木头打交道。
木头是有温度的,有纹理的,你用心待它,它就能变成一件有生命的东西。
可人心,怎么就比木头,还要冷,还要硬呢?
周三,林雪给我打了个电话。
这是她第一次,主动给我打电话。
电话里,她的声音很低,带着几分怯懦。
“爸,那份协议……准备好了吗?”
“准备好了。”
“那……什么时候签?”
“周六,你们回来的时候。”
电话那头,是一阵长长的沉默。
然后,她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,挂了电话。
我握着电话,心里五味杂陈。
我不知道我这样做,到底对不对。
我保住的,到底是一个家,还是一个家的空壳子?
周六,他们又回来了。
这一次,林雪的脸色更加憔悴。
她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,整个人像是被霜打过的茄子,蔫蔫的。
陈辉似乎也察觉到了她的不对劲,一路上都在嘘寒问暖。
“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了?要不跟公司请几天假,好好休憩一下。”
林雪只是摇头,不说话。
晚饭,依旧是我老婆子张罗的。
饭桌上,气氛比上次还要压抑。
吃完饭,我对我老婆子说:“你先回房看电视吧,我跟孩子们,有点事要谈。”
老婆子看了看我们三个,点了点头,没多问,就回房了。
客厅里,只剩下我们三个人。
陈辉一脸茫然地看着我。
“爸,什么事啊?这么严肃。”
我没看他,而是把目光,投向了林雪。
林雪的身体,不自觉地绷紧了。
我从抽屉里,拿出那份打印好的协议,和一盒印泥,放在了桌子上。
“这是什么?”陈辉拿起协议,看了起来。
他的眉头,越皱越紧。
脸色,也越来越难看。
“爸,你这是什么意思?财产公证?为什么突然要弄这个?”他抬头看着我,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和一丝愤怒。
“你别问我。”我指了指林雪,“你问她。”
陈辉的目光,转向了林雪。
林雪的头,垂得更低了,几乎要埋进胸口。
她的肩膀,在微微地颤抖。
“小雪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陈辉的声音,已经带上了严厉的质问。
林雪不说话,只是一个劲地掉眼泪。
“你说话啊!”陈辉的耐心,似乎到了极限,他猛地一拍桌子,桌上的碗筷都跟着跳了一下。
林雪被他吓得一哆嗦,哭得更凶了。
我看着眼前这一幕,心里叹了口气。
终究,还是要走到这一步。
“陈辉。”我开口,声音不大,却让陈辉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“你先别发火,听我说。”
我把上山采药,无意中听到林雪和她同事对话的经过,原原本本地,说了一遍。
我没有添油加醋,也没有任何情绪化的表达。
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实际。
一个,残酷的实际。
我说得很慢,很平静。
但客厅里的空气,却像是被抽干了一样,让人窒息。
陈辉的脸色,随着我的讲述,一点一点地,变得惨白。
他的眼神,从最初的震惊,到难以置信,再到最后的……绝望和痛苦。
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,他缓缓地,转过头,看着林雪。
那眼神,像是在看一个,他从来不认识的陌生人。
“她说的……是真的吗?”他的声音,嘶哑得不成样子。
林雪的身体,抖得像风中的落叶。
她没有抬头,只是一个劲地哭,一个劲地摇头。
“不是的……阿辉,你听我解释……”
“我问你,是不是真的!”陈辉几乎是吼出来的。
他的眼睛,红得吓人。
林雪被他的样子吓住了,哭声戛不过止。
她看着他,嘴唇动了动,最终,还是无力地,点了点头。
那一个点头,像是一把重锤,狠狠地砸在了陈辉的心上。
他踉跄着,后退了两步,一屁股,跌坐在了椅子上。
他双手抱着头,痛苦地呻吟着。
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……”
我看着他,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。
这是我的儿子。
我看着他从小长大,教他走路,教他说话,教他做人要正直,要善良。
我却没教过他,怎么去面对,人心的险恶和背叛。
客厅里,只剩下陈辉压抑的喘息,和林雪低低的啜泣。
我拿起桌上的协议,递到林雪面前。
“签了吧。”
我的声音,打破了这死一样的沉寂。
林雪抬起泪眼,看着我,又看了看失魂落魄的陈辉。
她知道,一切都完了。
她拿起笔,手抖得不成样子,连笔都握不住。
试了好几次,才在协议的末尾,歪歪扭扭地,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然后,是按手印。
鲜红的印泥,像血一样,刺眼。
我把协议收好,一式两份,一份放在了抽屉里,一份推到了陈-辉面前。
“这份,你收好。”
陈辉像是没听见一样,依旧呆呆地坐着。
我走过去,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“儿子,站起来。”
我的声音,似乎给了他一点力量。
他缓缓地,抬起头,看着我。
眼睛里,布满了血丝。
“爸……”他开口,声音里带着无尽的疲惫和迷茫,“我该怎么办?”
“日子,还得过下去。”我说,“怎么过,你自己选。”
我看了林雪一眼。
“是离,是合,你们自己决定。我跟你妈,不干涉。”
说完,我转身,走进了我的木工房。
我需要一个人,静一静。
那一晚,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。
我只听到,客厅里,断断续续地传来争吵声,哭泣声,和摔东西的声音。
我老婆子几次想出去看看,都被我拦住了。
“让他们自己解决。”我说,“我们老了,管不了了。”
后半夜,声音渐渐停了。
天快亮的时候,我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。
他们走了。
第二天,我走进客厅。
一片狼藉。
地毯上,是摔碎的茶杯。
沙发垫子,也掉在了地上。
我默默地,收拾着残局。
老婆子走出来,看着这一切,眼圈红了。
“老头子,他们……不会有事吧?”
“没事。”我把碎瓷片扫进簸箕,“年轻人,吵吵闹-闹,正常。”
我这么安慰她,也这么安慰自己。
但心里清楚,有些东西,碎了,就再也拼不回来了。
从那后来,很长一段时间,陈辉都没有再回来。
只是每周,会打个电话,报个平安。
电话里,他的声音很低沉,很疲惫。
我问他和林雪怎么样了。
他说,还在冷战。
我没再多问。
有些伤口,需要时间,才能慢慢愈合。
或者,永远也愈合不了。
那段时间,家里的气氛,很沉闷。
我老婆子的笑容,也少了。
她总是一个人,坐在院子里发呆。
我知道,她是在想儿子。
我把更多的时间,都花在了木工房里。
我开始雕刻一件复杂的作品。
是一对龙凤呈祥的摆件。
我想,等我雕好了,或许,他们的关系,也能有所缓和。
这只是一种,美好的愿望罢了。
日子,就在这沉闷的平静中,一天天过去。
转眼,就过了两个多月。
秋天来了。
院子里的核桃树,叶子开始变黄,一片片地往下落。
一个周六的下午,我正在院子里劈柴。
院门,突然被推开了。
是陈辉。
他一个人回来的。
他瘦了,也黑了,整个人看起来,沧桑了不少。
但眼神,却比之前,要沉静了许多。
“爸,妈。”他喊了一声。
老婆子听到声音,从屋里跑出来,拉着他的手,眼泪就下来了。
“你这孩子,怎么才回来啊!”
“公司忙。”陈辉笑了笑,笑容里带着几分苦涩。
他从车里,拎出大包小包的东西。
有给我们买的衣服,有老婆子爱吃的点心,还有我常喝的茶叶。
那天晚上,我们一家三口,吃了顿饭。
饭桌上,谁也没提林雪。
吃完饭,陈辉陪着我,在院子里散步。
“爸,那份协议,我去公证了。”他突然开口。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“房本的名字,也加上了我的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
“我们……还没离婚。”他看着天上的月亮,缓缓地说,“她说,她知道错了,想重新开始。”
我沉默着,没有说话。
“爸,你说,我该信任她吗?”他转过头,看着我,眼神里充满了迷茫。
我看着他,像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。
一样的执拗,一样的……心软。
我叹了口气,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“儿子,路是你自己的,要怎么走,得你自己拿主意。”
“婚姻,就像我们盖房子。地基打歪了,墙砌得再高,也是危房。”
“是推倒了重建,还是修修补补,接着住,得看你,还愿不愿意,住在这屋檐下。”
“也得看,那个跟你一起盖房子的人,是不是真心想把这房子,修好。”
陈辉低着头,沉默了很久。
“爸,我清楚了。”
那天晚上,他跟我说了许多。
说他这两个月的痛苦,挣扎,和反思。
他说,他恨林雪的欺骗和算计。
但他也承认,这几年,他忙于工作,的确 忽略了她,忽略了这个家。
他说,林-雪这些天,变了许多。
不再提钱,不再抱怨。
开始学着做饭,学着关心他。
每天晚上,都会等他下班回家。
“也许,她是真的知道错了。”他说。
我不知道。
人心,是最难看透的东西。
我只希望,我的儿子,不要再受到伤害。
又过了一个月。
陈辉带着林雪,一起回来了。
林雪瘦了许多,也憔悴了许多。
她看到我,眼神里有些躲闪,怯生生地喊了一声:“爸。”
我点了点头,没多说什么。
她不再像以前那样,巧笑倩兮,八面玲珑。
变得很沉默,很安静。
她会主动去厨房,帮我老婆子做饭。
会默默地,把我们换下来的脏衣服,拿去洗了。
吃饭的时候,她会先给我们盛好汤。
这一切,她做得小心翼翼,像个初来乍到的新媳妇。
我老婆子看在眼里,心里是高兴的。
她拉着我的手,悄悄说:“老头子,你看,小雪这是真的改了。”
我没说话。
我只是看着林雪忙碌的背影,心里在想,这到底是真心的悔过,还是更高明的……演戏?
我不知道。
我也不想去猜了。
日子,就这样,不好不坏地,继续过着。
他们回来的次数,渐渐多了起来。
每次回来,林雪都会带许多东西。
她给我老婆子买的那个按摩仪,老婆子每天都在用,逢人就夸,是儿媳妇孝顺。
她也给我买了一套新的木工工具,德国产的,很贵。
我收下了,但一次也没用。
我还是习惯用我那套,跟了我几十年的老伙计。
有时候,我看着这个家,会有一种错觉。
仿佛,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一切,都和以前一样。
但只有我自己知道,那根刺,一直扎在心里。
拔不出来,也咽不下去。
一碰,就疼。
冬天的时候,下了一场大雪。
整个村子,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
那天,是冬至。
按照我们这的习俗,要一家人在一起,吃顿饺子。
陈辉和林雪,一大早就回来了。
还带回来一个消息。
林雪,怀孕了。
老婆子听到这个消息,高兴得合不拢嘴,抓着林雪的手,一个劲地说:“太好了,太好了,我要抱孙子了!”
陈辉也一脸喜气,看着林雪的眼神里,充满了温柔。
我也很高兴。
或许,一个新生命的到来,能冲淡过去那些不愉快。
能让我们这个家,真正地,重新开始。
我们一家人,围在一起,和面,擀皮,包饺子。
其乐融融。
林雪的脸上,也露出了久违的,发自内心的笑容。
那一刻,我几乎要信任,一切,都过去了。
吃完饺子,陈辉和林雪要回城里。
临走前,林雪走到我面前,犹豫了很久,才开口。
“爸,对不起。”
她深深地,给我鞠了一躬。
“以前,是我不懂事,是我错了。谢谢您……没有放弃我,没有拆散我们这个家。”
我看着她,心里百感交集。
“过去的,就让它过去吧。”我说,“后来,好好跟陈辉过日子,好好把孩子生下来。”
“嗯。”她重重地点了点头,眼圈红了。
我看着他们开车离去,心里那块压了很久的石头,似乎,终于松动了一些。
也许,人,都是会变的。
也许,我该选择,信任一次。
日子,似乎真的,在一点点变好。
林雪怀孕后,陈辉脸上的笑容,也多了起来。
他们每个周末都回来,林雪的肚子,一天天大了起来。
她会拉着我老婆子的手,问许多关于怀孕和育儿的事情。
婆媳俩的关系,看起来,比以前还要亲密。
她对我,也多了一份,发自内心的尊敬和……敬畏。
有时候,她会坐在我的木工房门口,看着我做木工活,一看就是一下午。
她说,看着我把一块块木头,变成精美的物件,觉得很神奇,很安心。
我渐渐地,也放下了心里的芥蒂。
我想,或许,是我以前,太固执了。
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
知错能改,善莫大焉。
我甚至开始,用她给我买的那套新工具。
不得不说,德国的工艺,的确 好。
用起来,得心应手。
春天的时候,林雪生了个大胖小子。
七斤八两。
母子平安。
我当爷爷了。
我和老婆子,连夜赶到了市里的医院。
看着襁褓里,那个皱巴巴的小家伙,我心里,被一种从未有过的,柔软的情绪,填满了。
那是血脉相连的感觉。
是生命的延续。
我看着守在病床边,一脸疲惫却又满眼幸福的儿子。
看着躺在床上,面色苍白,却努力微笑的林雪。
我突然觉得,以前那些事,好像,真的不那么重大了。
只要他们好,只要这个家好,比什么都强。
孙子满月的时候,我们在老家,办了满月酒。
请了许多亲戚朋友。
很热闹。
席间,林雪抱着孩子,走到我面前。
“爸,给孩子,取个名字吧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你们没想好吗?”
“想了几个,但阿辉说,孩子的名字,得您来取。”
我看着她怀里,睡得正香的孙子。
他那么小,那么软。
我想了想,说:“就叫……陈安吧。”
“平安的安。”
“我不求他将来,大富大贵,光宗耀祖。”
“我只希望他,一辈子,平平安安,顺顺利利。”
“陈安。”林雪念了一遍,笑了,“好名字。谢谢爸。”
那天,我喝了许多酒。
很高兴。
我以为,我们这个家,终于,雨过天晴了。
我以为,往后的日子,就会像孙子的名字一样,平安,顺遂。
可我,终究还是,想得太简单了。
孙子半岁的时候,我那个当律师的远房侄子,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。
电话里,他的语气,很奇怪。
“二伯,您在家吗?我有点事,想跟您当面说。”
我心里,咯噔一下。
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下午,他开车来了。
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。
他从公文包里,拿出了一份文件。
“二伯,这是我一个朋友,在房管局工作的,前几天,无意中查到的东西。”
他把文件,推到我面前。
是一份,房产交易的备案记录。
上面,是城里那套房子的地址。
交易时间,是三个月前。
买方的名字,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。
而卖方那一栏,签着两个名字。
陈辉。
林雪。
我的脑子,嗡的一声,一片空白。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?”我的声音,在发抖。
“他们把房子,卖了。”侄子说,“而且,是瞒着您卖的。”
“卖了?”我像是没听懂一样,重复了一遍。
“那……那他们目前住哪?”
“他们租了个房子。而且……”侄子顿了顿,似乎在犹豫,该不该说下去。
“而且什么?”我急切地问。
“而且,我查到,林雪用这笔卖房的钱,注册了一家公司。”
“公司的法人代表,是她自己。”
“公司的最大股东,是一个叫……方芳的人。”
方芳。
这个名字,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我的记忆。
就是那个,在山上,和林雪一起,出谋划划的女人。
我浑身的血,都凉了。
我清楚了。
所有的一切,我都清楚了。
什么真心悔过。
什么重新开始。
什么婆慈媳孝。
全都是演戏。
一场,演了将近一年的,天衣无缝的大戏。
她的目的,从始至终,就只有一个。
钱。
那套房子。
她用怀孕,用孩子,博取了我们的信任,博取了陈辉的原谅。
然后,在我,在我们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的时候,给了我们,最致命的一击。
她让陈辉,心甘情愿地,在卖房合同上,签了字。
她甚至,连那份我们签过的协议,都算计进去了。
协议规定,如果他们离婚,我们出的那八十万,要还给我们。
可他们,没离婚。
他们是“共同”,把房子卖了。
从法律上,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好一个,林雪。
好一个,高材生。
好一个,做会计的。
算得,真精啊。
我瘫坐在椅子上,看着满院子的阳光,却只觉得,浑身冰冷。
我像个傻子。
一个,被耍得团团转的,老傻子。
我以为我赢了。
原来,从头到尾,我都在她的算计里。
我输得,一败涂地。
“二伯,您别太激动。”侄子担忧地看着我。
我摆了摆手。
我没有激动。
我的心里,一片死寂。
哀莫大于心死。
这一次,是真的,死了。
我拿起手机,颤抖着,拨通了陈辉的电话。
电话响了很久,才被接起。
“喂,爸。”陈辉的声音,听起来有些疲惫。
背景音里,有婴儿的哭声。
“你在哪?”我问,声音平静得,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怕。
“我在家啊,怎么了,爸?”
“哪个家?”
电话那头,沉默了。
过了很久,陈辉才用一种,近乎于哀求的语气说:“爸,你……你都知道了?”
“是。”我只说了一个字。
“爸,你听我解释。小雪她……”
“我不想听她。”我打断他,“我只想问你,我的孙子,陈安,目前在哪?”
“安安在……在我身边。”
“好。”我说,“你目前,立刻,马上,带着我的孙子,回老家来。”
“我给你,一个小时的时间。”
“如果一个小时后,我看不到我的孙子。”
“我就报警。”
“我说到,做到。”
说完,我挂了电话。
我看着院子里的那棵老核桃树。
今年的核桃,结得特别好。
一个个,青皮饱满。
再过不久,就能收了。
可这个家,还能等到,收获的那一天吗?
我慢慢地站起身,走进我的木工房。
我拿起一把斧子。
那是我用了几十年的老伙计。
斧刃,依旧锋利。
我走到客厅,看着墙上,挂着的那张全家福。
那是孙子满月的时候照的。
照片上,我们每个人,都笑得很开心。
我举起斧子,狠狠地,朝着那张照片,劈了下去。
哗啦一声。
玻璃碎了一地。
幸福的假象,也跟着,碎了一地。
我,陈建军,一个老木匠。
我盖了一辈子的房子,修了一辈子的家具。
我以为,我能修好,这世上所有坏了的东西。
可我错了。
有一种东西,坏了,就再也修不好了。
那就是,人心。
尾声。
我的手机,突然响了一下。
是一条短信。
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我打开。
上面只有一句话。
“伯伯,我是方芳。林雪她,不止是图钱那么简单。她拿到了陈辉公司核心技术的代码,卖给了对家公司。你快让陈辉看看他的电脑。”

我看着那条短信,手里的斧子,“哐当”一声,掉在了地上。